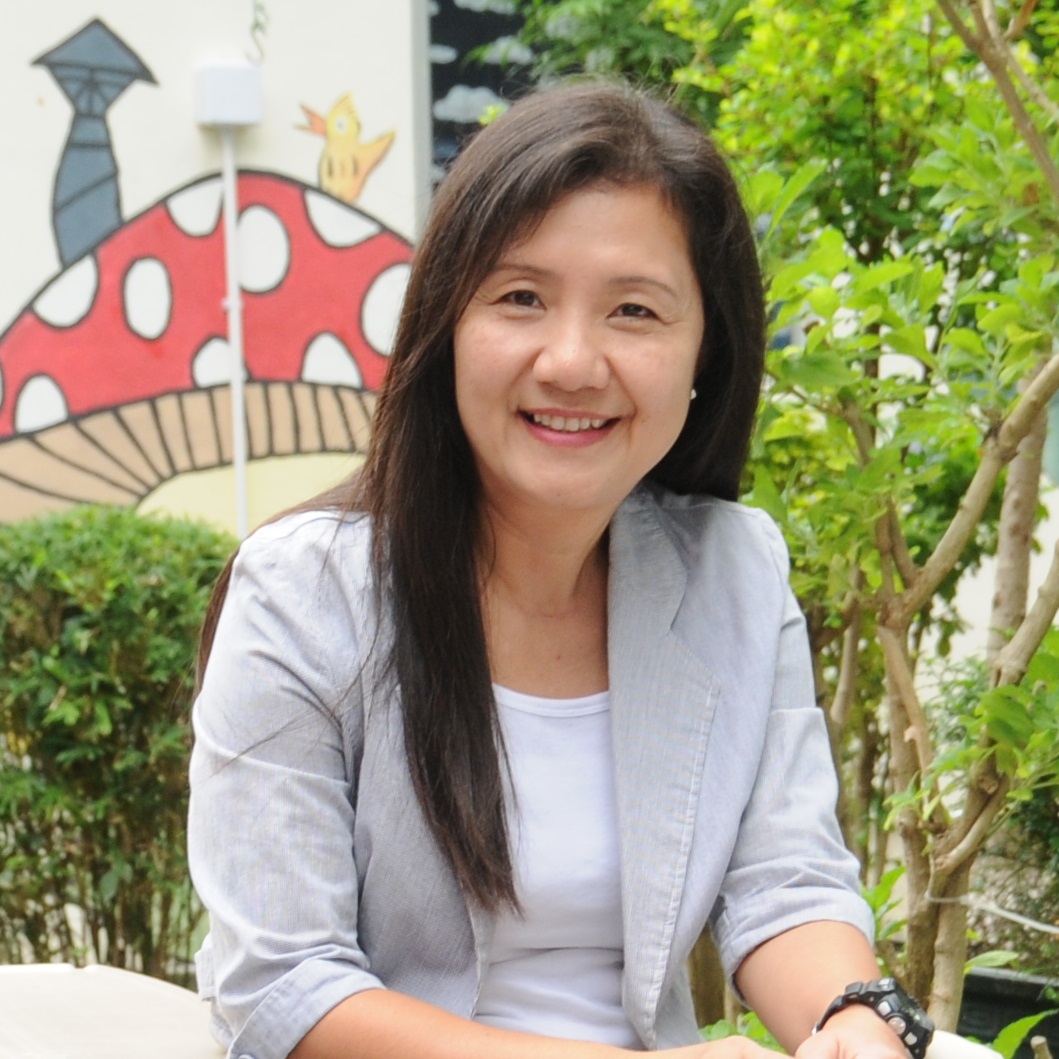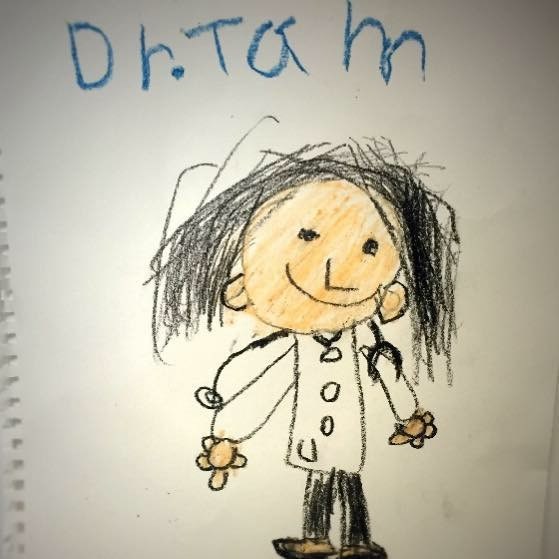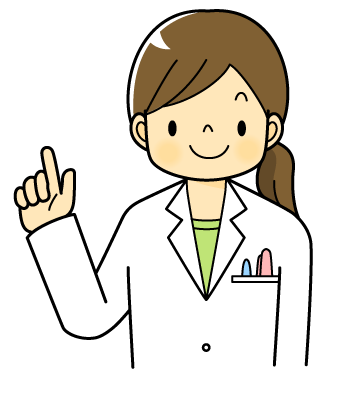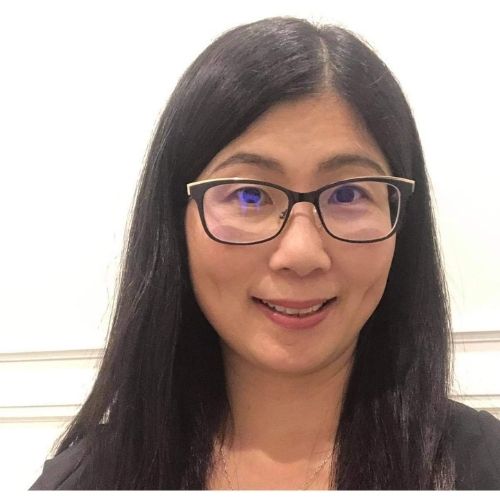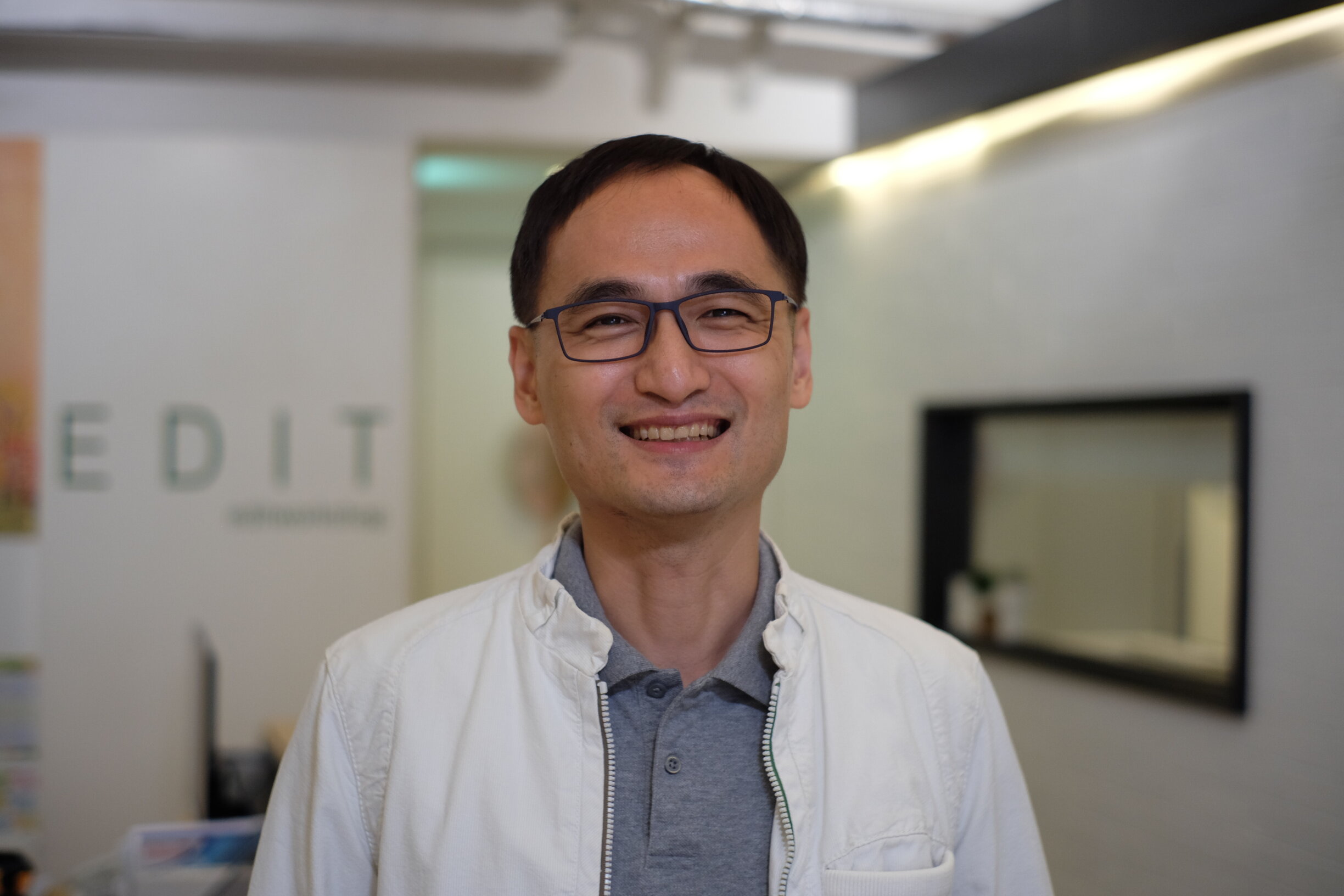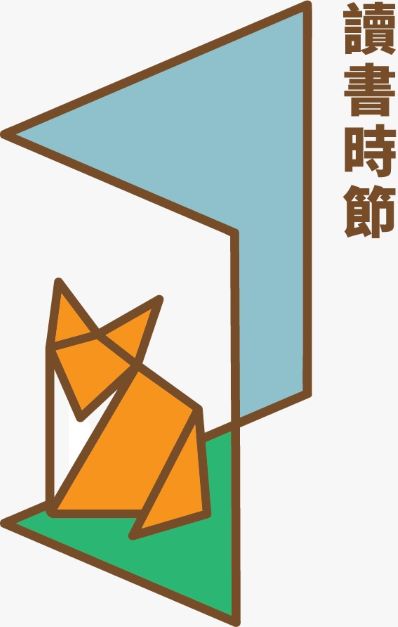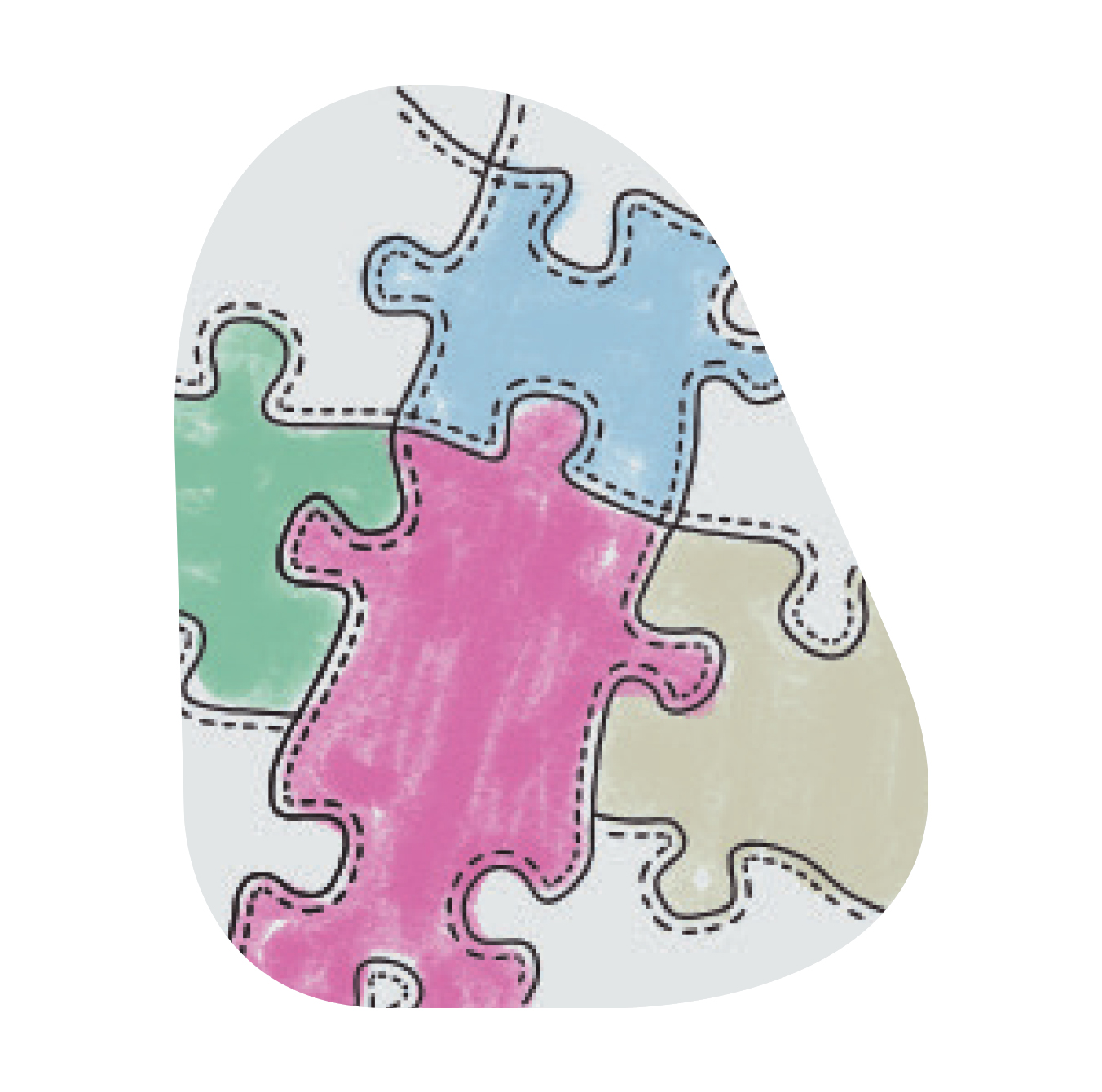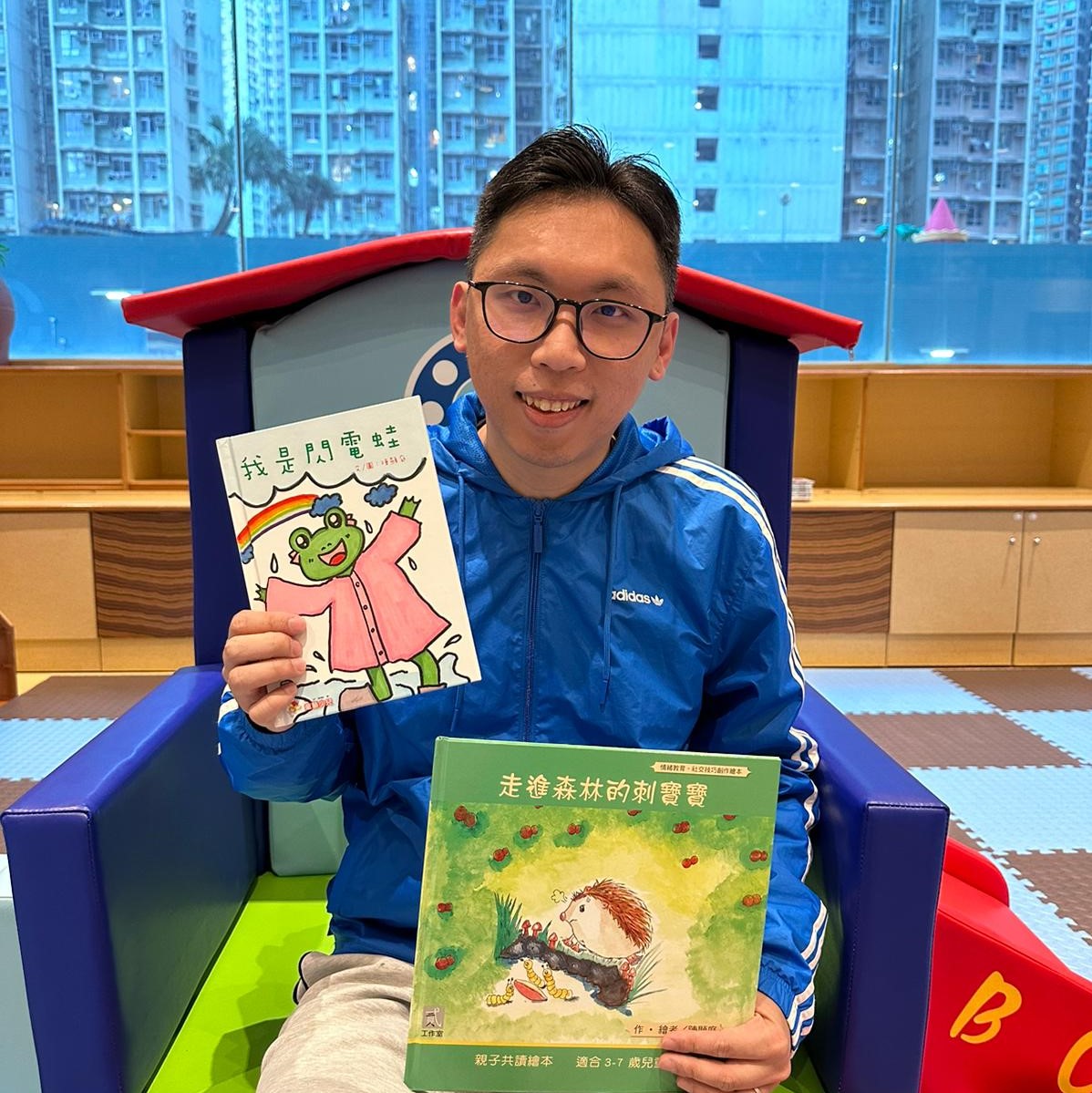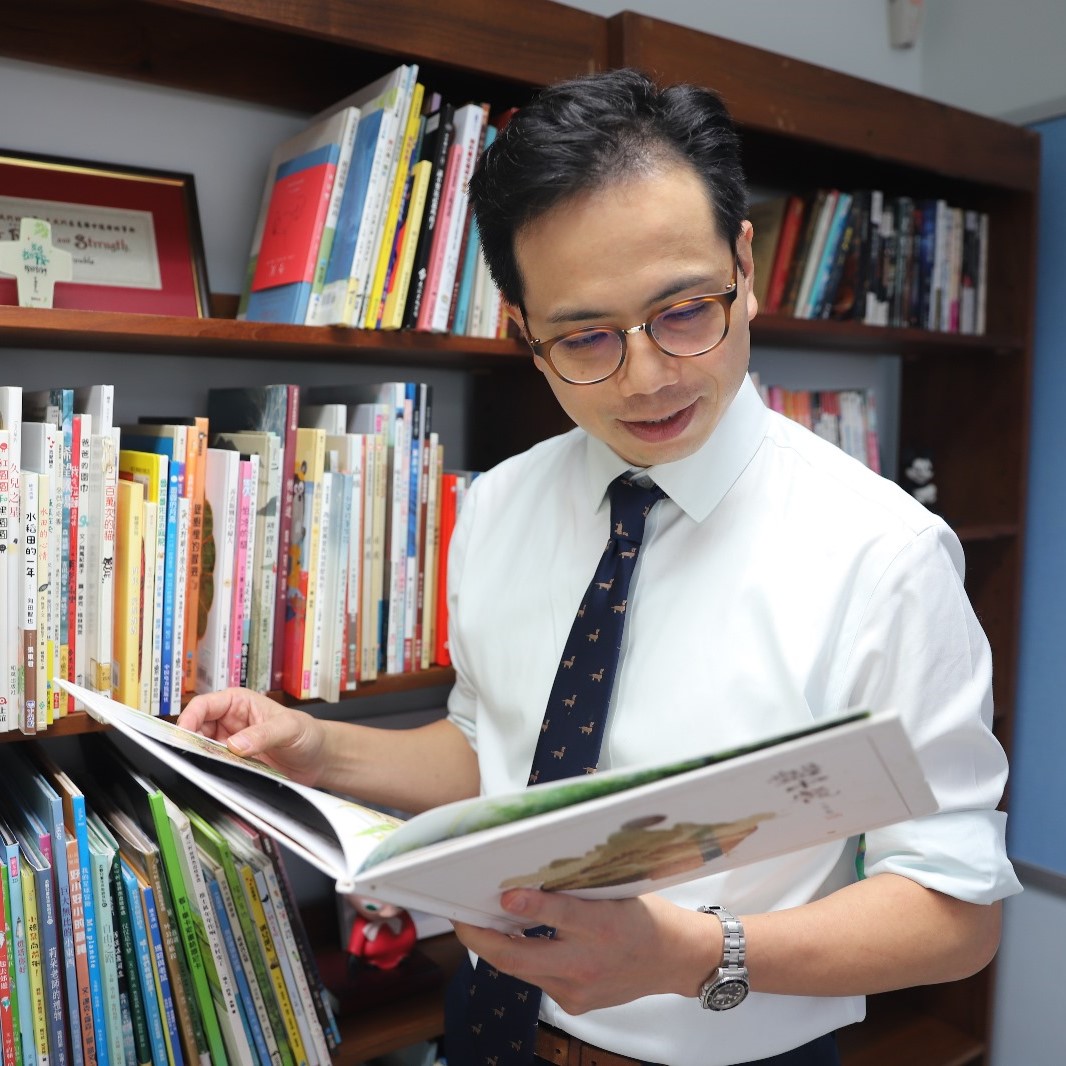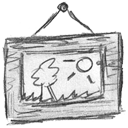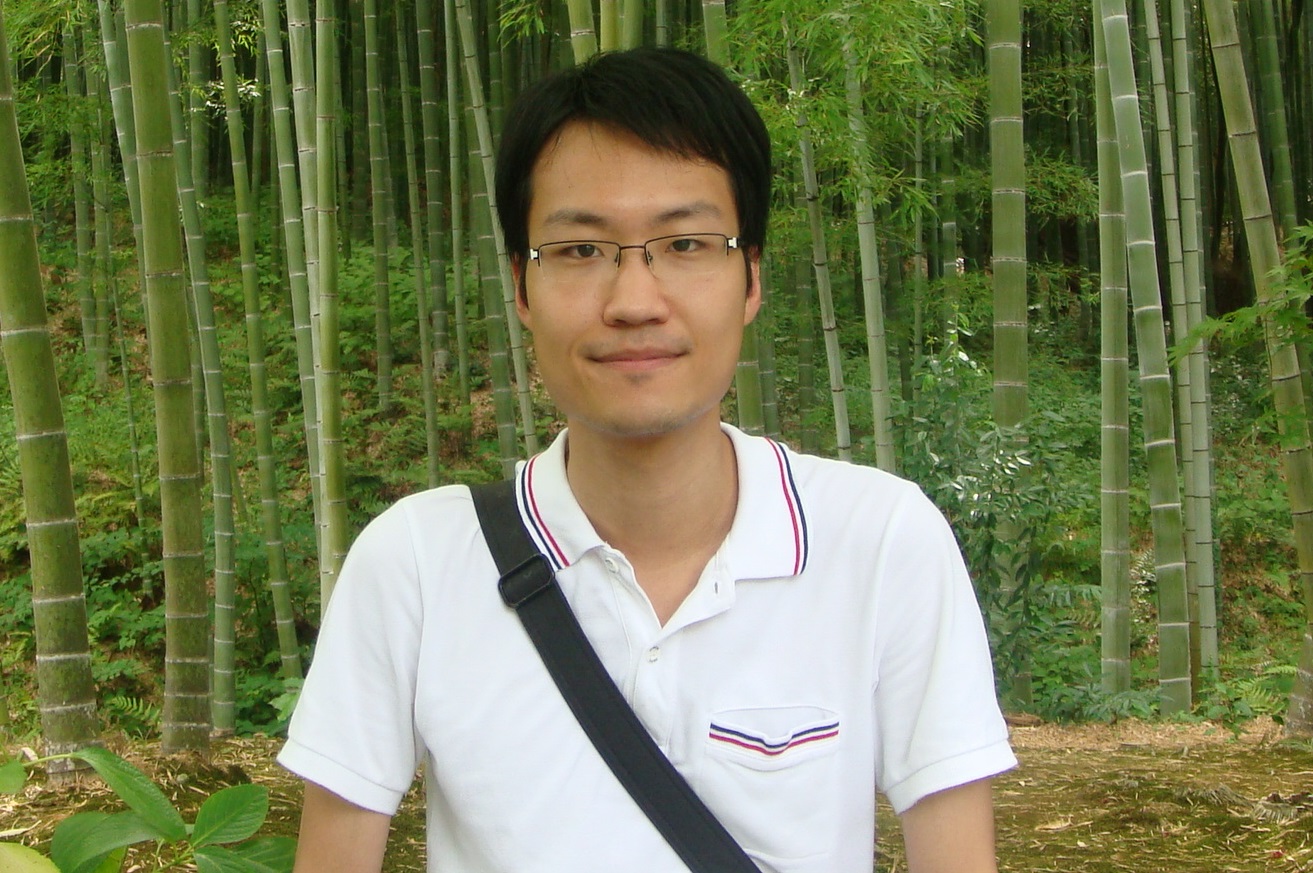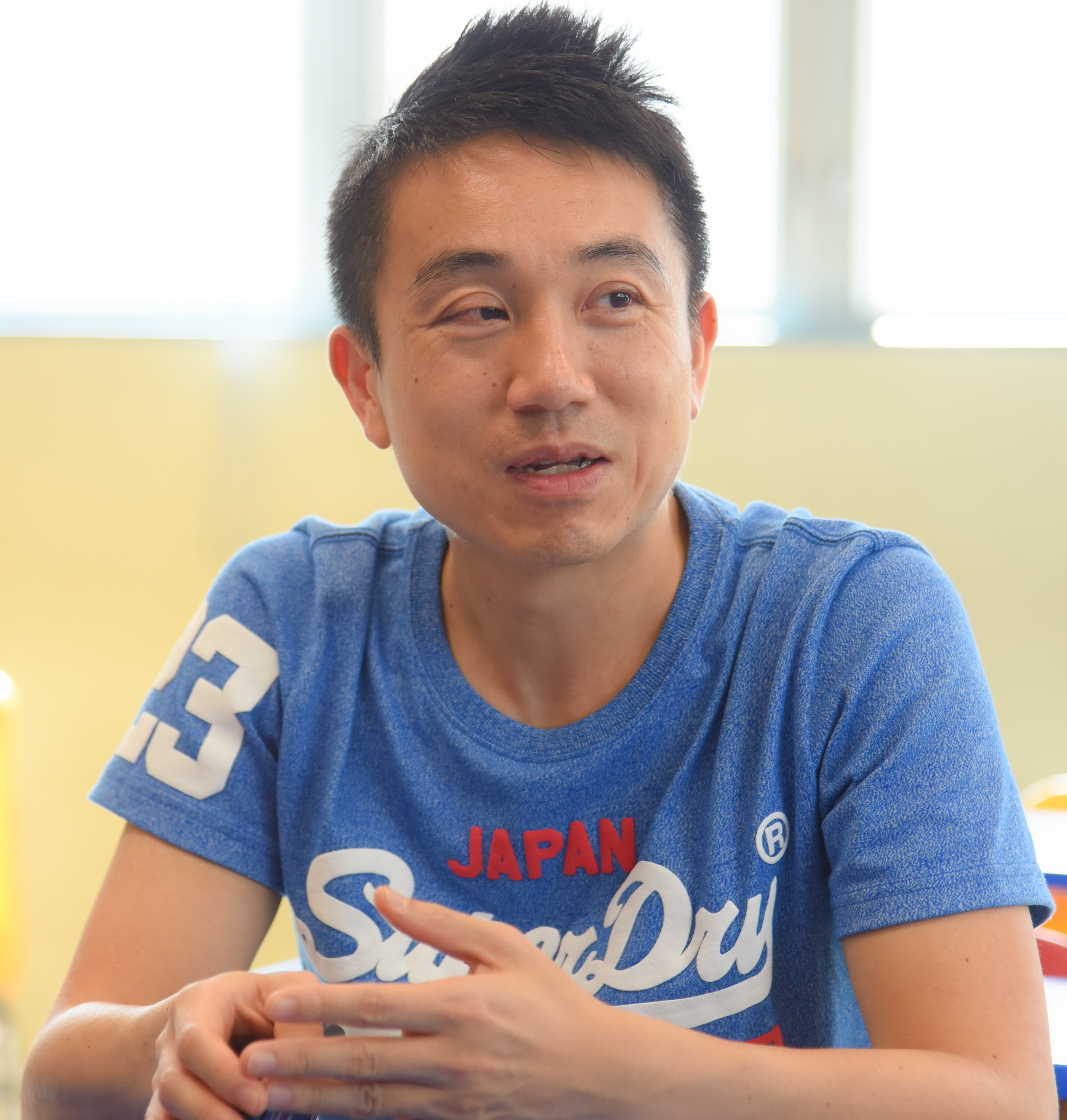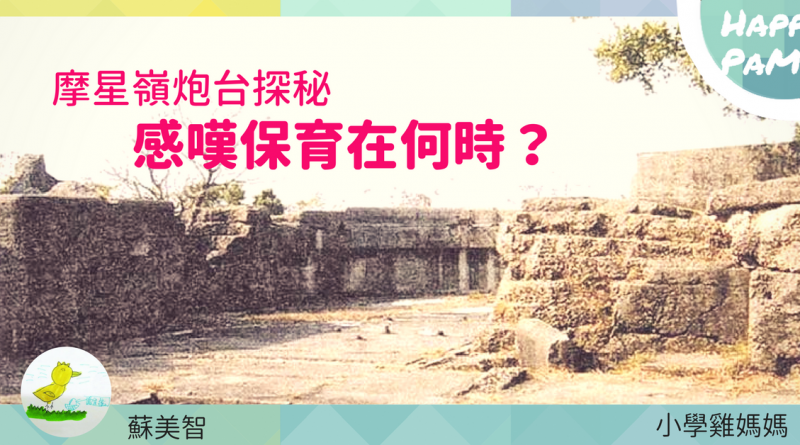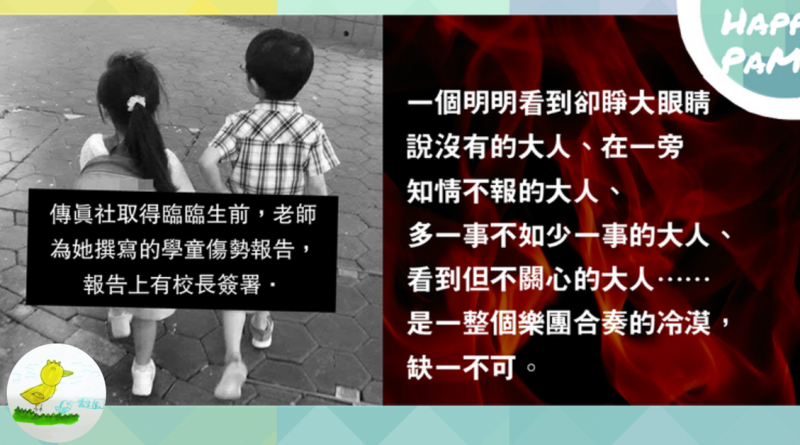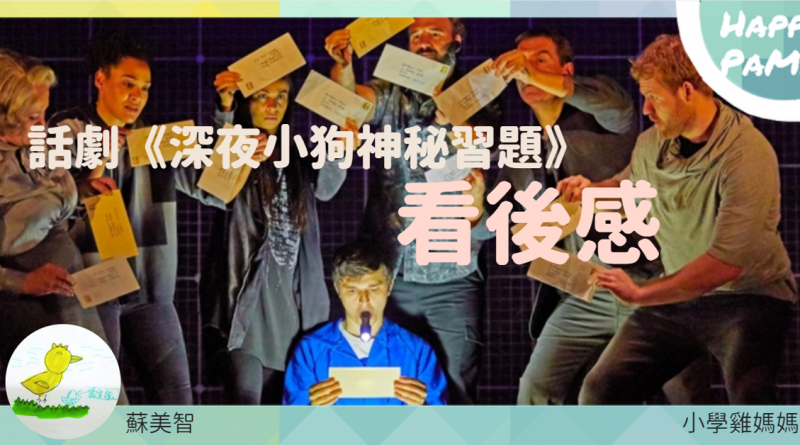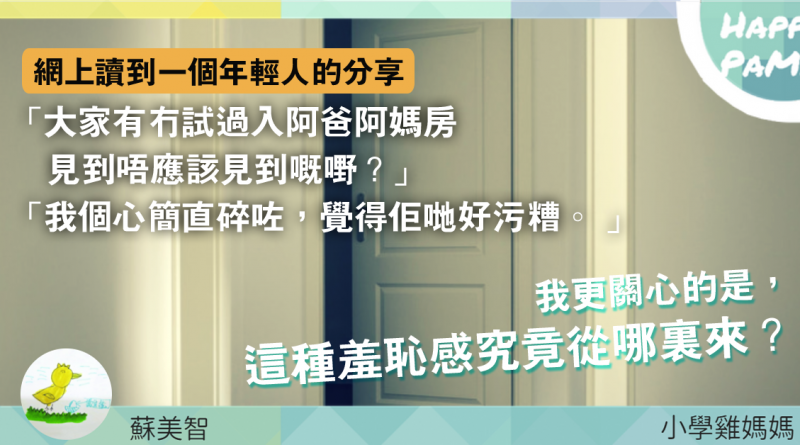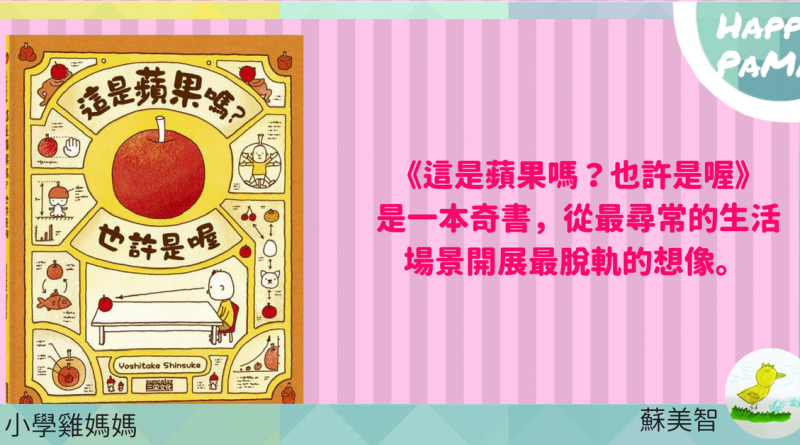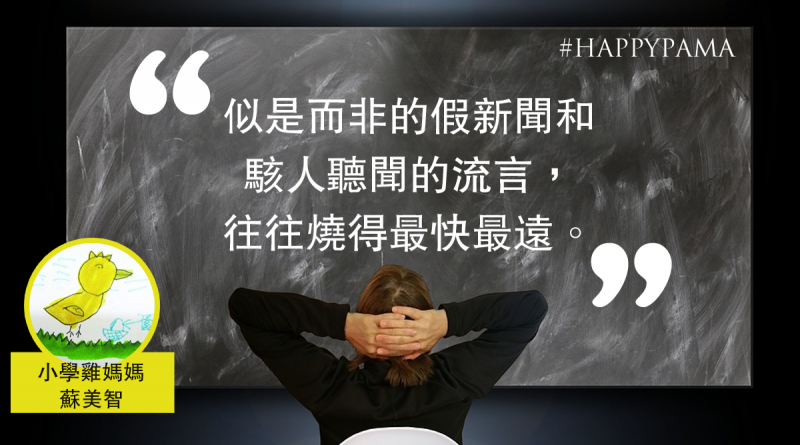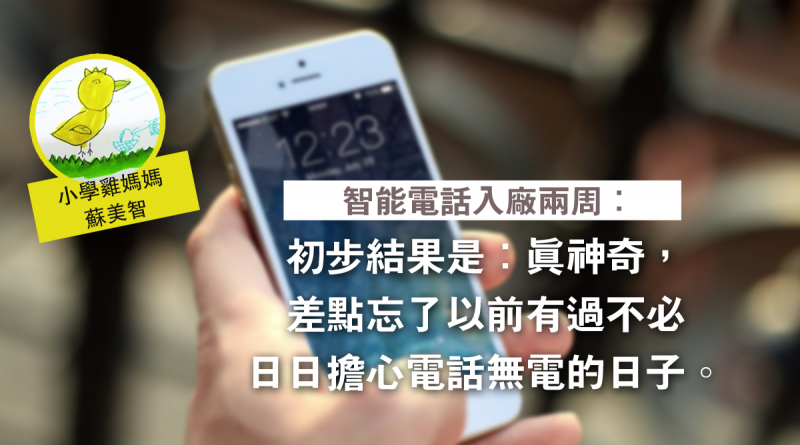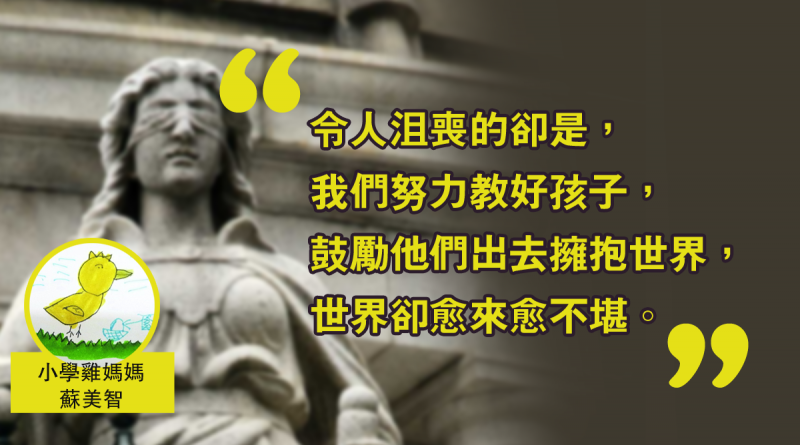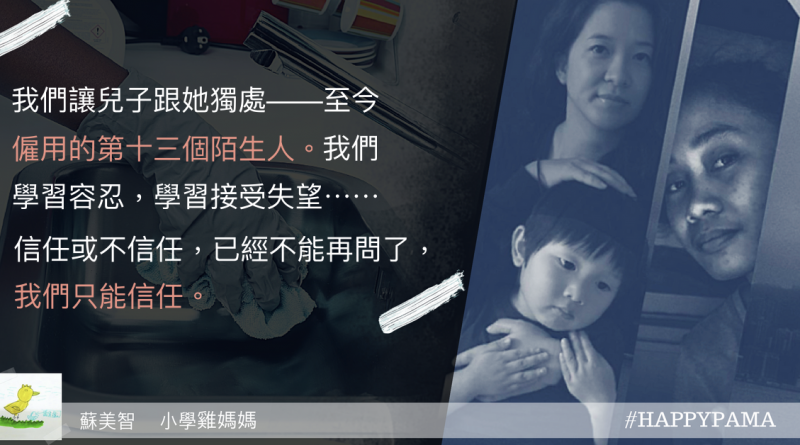小學雞媽媽:摩星嶺上的悲壯
復活節,人家到外地旅行,我們留在香港,跑上摩星嶺青年旅舍宿營。旅舍的日落風景絕好,職員人情味也濃,可是令人印象最深刻的,始終是附近的摩星嶺炮台古蹟。對於這組自20世紀初便矗立港島西的軍事建築群,真慚愧,我們之前從未踏足,所以非常驚喜。現場規模大,建設也多樣,營房、軍火庫、防空通道、偽裝牆、運送炮台的大斜坡等,四通八達,拐個彎又是另一組設施,走來走去走不完,很有探險的樂子。 據民間組織摩星嶺之友整理的資料,英軍在1900年已經計劃在此興建軍防,以扼守維多利亞港西部和硫磺海峽等航運要道。那是滿清末年,朝廷積弱,西方列強對中國這塊肥肉苦視眈眈,所以英國在香港這個東亞港口設置重型炮台,對準的其實是法俄的軍事威脅,以守護自己的殖民利益。 我家小子心血來潮,要為昔日要塞畫一幅平面佈置圖,掏出筆紙便在路上用功。 港淪陷 英軍自毁要塞設施 摩星嶺的軍事設施終於在1912年全部完成,沒想到它真正派上用場,卻是差不多30年後的事,而且只挺了短短17日。1941年12月8日,日本向香港發動攻擊,摩星嶺要塞成為支援港島東部和中部的主要火力,其間受到劇烈轟炸;16日,位於山頂的指揮總部被毁;25日,香港總督楊慕琦爵士宣布無條件投降,香港陷入黑色聖誕;同一時間,摩星嶺上的守軍炸毁殘餘設施,以免落入敵軍手中。 走着走着,不禁遙想上世紀在這個山頭上發生的悲壯。我家小子心血來潮,要為昔日要塞畫一幅平面佈置圖,掏出筆紙便在路上用功。這工夫殊不簡單,既要繪畫出各種建築結構,又要考慮現場山勢的高低起伏,小子愈畫愈吃力,眼看差不多日落西山,筆下的平面圖不同空間之間,依然難以合理地拼合——這其實是大人應該做的工作。我們身處的炮台現場,建築群的平面圖固然欠奉,就連文字資料也貧乏得令人氣結,只幾處豎起說明牌,還是一樣的介紹文案,寥寥幾句非常單薄,真對不起這些豐富的建築和那段關鍵的歷史。 務請珍重,不要讓戰時文物湮沒在雜草和垃圾當中。 戰時文物 保育在何時? 上網查找,除了看到民間組織摩星嶺之友倡議保育歷史外,也看到中西區區議會在2014年與古物古蹟辦事處的信件往來,討論為這組二級歷史建築物設立歷史徑的建議。可是4年過去了,不知後續如何?務請珍重,不要讓戰時文物湮沒在雜草和垃圾當中。
詳細內容